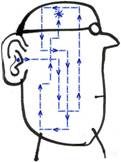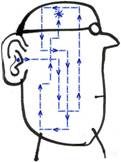不妨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的用餐礼仪都很得体,但却长着蜥蜴的耳朵,那么席间的交谈将会是怎样?我们不但在想说话时停止吃饭,而且由于耳朵的一部分附着在下颚上,还不得不在听别人说话时也停止吃饭。既然餐桌上没有餐具在动,服务员因此会认为我们“已经用完餐了”,就会把餐盘中尚未开吃的食物撤走。
进化中的“圣杯”
有时候,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对我们的生活却关系重大。这里要说的是隐藏在人体耳道中的3块最细小的骨头(鼓膜内侧)。这3块小骨都有乐器般的名称:锤骨、砧骨和镫骨,个头非常非常小,只有小水珠那么一丁点儿。但它们却共同构成了生物演化史上最伟大创造之一的基础,那就是哺乳动物的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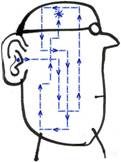
中耳给了我们单独的声音接受系统,给了我们咀嚼的能力,使我们不再在吃饭时对外界“置若罔闻”;而大多数其他脊椎动物仍然是这样。要不是我们的祖先替我们练就了一副实用的颚骨,谁也无法保证我们人类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仍能“喋喋不休”。
中耳也解释了为什么哺乳动物这个群体拥有地球上最敏锐的听觉和最多样的听觉方式,蝙蝠和海豚能探测到从物体尖端反射回来的超声压力波,大象和座头鲸能听到次声波,捕捉到同伴在几英里外发出的低声长啸。总之,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中耳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创造,是哺乳动物身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天然的或更古老的模式能够代替它。
古生物学者在2009年10月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报告发现了距今约1.23亿年的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这个体重约3盎司,个头跟花栗鼠差不多大的动物化石被命名为亚洲毛兽。该动物化石特别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的耳朵。保存完好的化石显示,亚洲毛兽的中耳属于过渡型中耳,一半像哺乳动物、一半像爬行动物。考虑到化石的年代以及来自更早哺乳动物化石的证据,研究人员相信,亚洲毛兽表现为一种返祖现象,一种向更古老听觉器官结构的逆转。
到了现生哺乳动物的祖先崛起之时,其遗传特征就已经被固定了下来。在已知的大约5400种哺乳动物中――无论是胎盘类哺乳动物、有袋类哺乳动物,还是有鸭嘴的卵生单孔类动物――每一种都有3块小骨从下颚骨完全游离出来构成独立的耳朵,且始终如此。
位于匹兹堡市卡内基自然史博物馆的古脊椎动物学主任、文章的作者之一罗哲西(Zhe-Xi Luo)认为:“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哺乳动物进化的人来说,中耳的进化就是一只圣杯。敏锐的听觉使得早期哺乳动物与恐龙共存成为可能,这确实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说,新的化石“让我们看到了哺乳动物身上这一重要特征背后的复杂进化历程。”
精湛的“测音师”
《人是怎么来的:35亿年的人体历程》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有机生物学和解剖学教授尼尔·舒宾(Neil Shubin)指出,大自然以谵妄的方式自行其道,“这篇文章说明,哺乳动物的耳朵不是以直线方式进级的。它要么是独立地进化了好多次,要么是反反复复,有退有进。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议论的是一丛枝叶繁茂的灌木。”
这一发现也与最近在分子遗传学和发生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相吻合。在现生哺乳动物中,胚胎的中耳是最后成熟并最后转移到合适位置的结构。即使在出生后,这些小骨仍有可能保留着所谓的麦氏软骨――在胚胎早期连接耳与颚――的一些蛛丝马迹。罗哲西博士及其同事们提出,负责这一晚阶段脱离的发育定时基因的突变可能从本质上把亚洲毛兽的耳永久性地锁定在了胚胎状态,就像罕见的人类颅面部异常,如颅面部骨发育不全综合征。罗哲西指出,化石研究者、发生生物学者和医学遗传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
研究人员早就知道,哺乳动物的中耳骨骼进化自爬虫类祖先的颚骨,进化自这些骨骼的“目的重建”, 就像舒宾博士说的那样:为了与哺乳动物齿系的精致和精密而平行发生的听力改进。舒宾说的“爬行动物用多块骨头构成颚,而哺乳动物只用一块骨头。”爬行动物的牙齿简单,通常呈锥形,凌乱地排列在口中;而哺乳动物有配套的臼齿、两尖齿和犬齿,上、下颚牙齿咬合时成直线。华盛顿大学的哺乳动物进化学专家克里斯蒂安·A·赛德(Christian A. Sidor)说:“我们看到哺乳动物实际上是在咀嚼食物。”
研究人员指出,推动哺乳动物中耳进化的一个选择性压力可能是为了得到稳定的昆虫供应需求,即使是非食虫的人类也保持着对高音调噪音――如蚊子的嗡嗡声――的异常敏感。

耳道示意图
哺乳动物的耳朵也是一个精于探测微弱声音的大师:当一个传进来的压力波推动鼓膜及其邻近的小骨时,这些小骨的支点运动能在传送压力波前将其放大。早期的哺乳动物很可能是夜行性的,夜间活动能够较好地避开白天捕猎的恐龙。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哺乳动物仍然偏爱在天黑后出来猎食。罗哲西博士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精巧的感觉系统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夜间环境的基本要求。”
同样道理,我们在与善言的朋友共进烛光晚餐时也少不了它。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