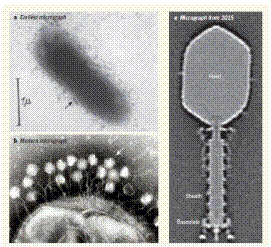作为感染细菌细胞的小型病毒,噬菌体首次发现于1915年,百年以后的今天,这些噬菌体对基础生物学、生物技术和人类健康的科研贡献仍然行之有效、没有减退,它们的百年华诞值得我们庆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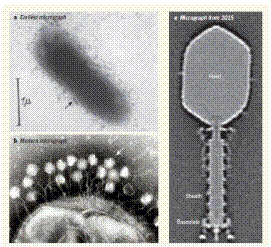
图1噬菌体形态 感染细菌的病毒首次描述于1915年,但是一直到了1940年才有了第一张噬菌体(箭头)感染细菌的电镜图发表(图1a)。这些早期的图像帮助证实了,这些归因于噬菌体的效应事实上是由病毒导致的,而不是由酶活性造成的。现代电子显微镜(图1b、1c)得到的噬菌体图像揭示了噬菌体的结构和感染过程
1915年,细菌学家弗雷德里克·图尔特(Frederick Twort)发表了第一篇描述噬菌体类病毒的论文,它们可以感染细菌,在细菌体内繁殖自己并杀死细菌细胞。从那以后,对这些病毒的研究,给生物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把这些病毒命名为噬菌体。噬菌体为20世纪的分子生物学革命提供了实验体系和工具,它们的快速发展已经使生态学和进化的基础原理得到了检测。现在,我们知道了噬菌体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生物学实体,它比任何其他生命形式都更加丰裕和具有遗传多样性。尽管它们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迷人的实体的研究仍然还是一种小而全的科学行为。在此,我们简要地回顾噬菌体研究的历史,希望给新一代的噬菌体科学家们带来鼓舞和激励。
在20世纪早期,大多数噬菌体科学家都对使用病毒作为抗细菌生物感兴趣。这是一个不受控制的科学试验时代,人们被注射以噬菌体,病毒被向水井中倾倒,都是为了希望杀死病原体性细菌、比如导致霍乱的细菌。正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抗生素,使这样的研究路线得到了戏剧性的减少。但是今天,由于抗生素抗性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事实,“噬菌体疗法”的概念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其后,噬菌体科学的发展进入了定量王国,一个研究网络,由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并命名为“噬菌体群”,使用这些病毒作为模型,进行生命是如何工作的前沿研究。1952年,阿尔弗雷德·赫尔希(Alfred Hershey)和玛莎·蔡斯(Martha Chase)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用一台高速离心机将放射标记的噬菌体从细菌细胞中去掉,帮助科学家们认识到DNA是遗传物质,这项实验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通过实验发现了许多噬菌体编码的DNA操作酶,比如DNA和RNA聚合酶、连接酶、核酸内切酶和核酸外切酶,接连不断地催生了分子生物学新认识、发展了生物技术产业。现在,世界各地每天都在使用着噬菌体蛋白质。限制性酶类保护着细菌免受噬菌体感染,为分子生物学家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这种趋势持续到了今天,正如人们所见,研究细菌如何防御噬菌体,使得科学家发现了CRISPR-Cas系统,随之才有基因组编辑革命的到来。
随着遗传学密码在20世纪中期得到了解析,对一个完整的基因组进行测序成为了首要的研究目标。噬菌体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目标,因为它们的基因组非常微小、还可以产生大量的DNA用于测序。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和同事们于1977年完成了对ΦX174噬菌体的整个基因组的测序,其测序技术在后来几十年中的细胞基因组测序中得到了沿用。随着更多其他噬菌体基因组测序完成,人们发现噬菌体可以在个体之间交换基因和大片断的DNA,这种水平基因转移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于遗传变异性产生的认识。海洋噬菌体群落是第一种被“鸟枪测序”的生物体,它催生了元基因组学(又称宏基因组学)的产生,也就是对微生物群落中所有成员进行大规模测序(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
认识噬菌体已经帮助我们建立了对宿主细胞和疾病的基础认识。噬菌体整合入细菌基因组后,可以戏剧性地改变它们的细菌宿主的特征,这些宿主中最为致命的细菌性病原体,比如霍乱弧菌、志贺菌和沙门菌等,许多就是通过这种机制来获得毒性因子的。分析噬菌体复制的生物学还揭示了噬菌体生命周期所需要的几种关键宿主编码因子,比如DNA旋转酶和“分子伴娘”蛋白质复合体GroEL和GroES。
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公开宣布“对癌症作战”,噬菌体生物学家们被招募,活跃地参与到这场人体生物学研究之中。基于认识到噬菌体编码了一些蛋白质,类似于宿主的蛋白质,这些科学家们在人类基因组中寻找与其他病毒内基因相似的基因。他们不仅发现了这些基因,还建立了“原癌基因”的概念,它们存在于人体基因组中,当其突变时,是癌症的主要病因。
另外一些噬菌体研究人员进入了DNA诱变、修复和重组的领域,建立了今天我们对癌症认识的基础。例如,科学家们认识到预先存在的突变可以使得细胞个体具有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生长优势,从而引发这样的理念:癌症细胞荷载有数十种预先存在的突变,它们可能与真实的肿瘤相关、也可能不相关。在艾滋病流行以后,噬菌体研究人员们打开了大门,认识到了逆转录病毒是如何整合入人类基因组的、什么样的宿主蛋白质参与其中。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热闹的噬菌体研究之后,噬菌体科学家们转向了不同的研究舞台、对噬菌体的研究大幅度降温。对于生物学家们的铁锤来说,噬菌体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铁砧,为什么现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呢?一个原因可能是,正如在任何旧科学学科中频繁发生的那样,人们的认识如同文献一样,经历了一种由博返约的过程,噬菌体也是如此。为了有助于应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了一些认识噬菌体的指导原则:
一个关键点是噬菌体对生物学多样性的贡献。在地球上大概有超过1 031种噬菌体颗粒,每种细菌细胞则有大约10种噬菌体颗粒。在人体中,两个个体之间主要的遗传差异是他们胃内的噬菌体。在其他作用中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病毒形成了适应性强的免疫系统,其基础是应用了免疫球蛋白样蛋白质结构域高度可变的特性,类似于抗体的使用机理(以变应变)。
一个概念是噬菌体携带的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参与了调节宿主的基础生理学过程,比如新陈代谢和抗生素抗性。有个迷人的例子发生在海洋蓝藻细菌的光合作用中,这些细菌产生的光收集触角复合体的部件在噬菌体感染后是高度不稳定的、易于腐败。但是噬菌体携带的基因可以编码受损蛋白质的替代品,使得细菌得以持续产生生物质,而噬菌体如同爆炸般产生大量后代。因此,这些海洋噬菌体通过增加光合作用的效能和产量,对海洋碳的巨量转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一种教训是任何细菌细胞的小而全的空间结构是由其噬菌体决定的。进化关系紧密相关的细菌之间的主要基因组学差异来源于整合进来的噬菌体(原噬菌体)及其基因组学事件,从插入或缺失到重大重排,有助于保卫细菌免受噬菌体感染。这种从不停止的由其噬菌体施加于细菌的选择压力是“红皇后假说”的最佳特征性的例子,也就是说,出于生存的需要,捕食动物与被捕食动物必须持续不断地进化。
展望噬菌体,它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这些种类的病毒相对容易合成,它们的基因组拥有模块化的特征,迎合了合成生物学家们的需要、对生物学功能进行工程化研究和实施。值此噬菌体被发现10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我们的生物学家伙伴们,放弃他们的细胞中心习惯,拥抱噬菌体吧!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
――――――――
本文作者弗瑞斯特·罗韦尔(Forest Rohwer)、安卡·M·西格尔(Anca M. Segall),现供职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生物学系病毒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