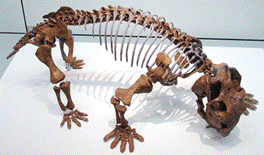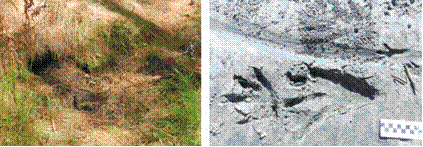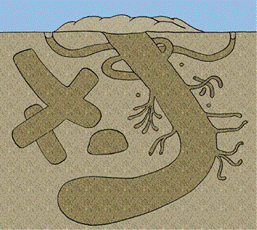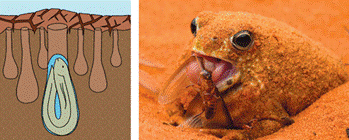许多动物会挖掘巢穴抵御来自天气、灾难或天敌的侵袭,当一些物种因侵袭灭绝时,它们幸存下来。

路易斯安那州洛克菲勒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短吻鳄躲藏在河边的洞穴里。这种洞穴可以帮助它们躲避炎热、干燥或寒冷的气候条件。移入地下的自我保护方式在它们和其他洞穴生物的进化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短吻鳄的巢穴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内居的鳄鱼藏在倾斜坑道的黑暗空间里,巢穴的入口常常在松树林中,为1米宽、呈半月形的洞。短吻鳄出现的时候往往先发出巨大的叫声,接着是张口的嘶嘶声。巢穴里的空间增加了这些声音的共振,把原本已经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惊悚。这种声音的组合更像是一种警告,效果俱佳,令我们所有人一起发出“哇!”的惊叹,同时后退几步,不得不掂量自己的处境。
这是我教学生涯的另一个时刻,我不知道有多少别的教授必须关注课堂上出现的食肉动物。尽管如此,如果我的学生对他们的课程材料没有兴趣,他们现在又非常忙碌,但或许也想知道与短吻鳄相关的事会不会出现在下一次考试中。
2013年3月,我们到佐治亚堰洲岛进行春假实地考察的第6天,我教的本科生、系里的同事、还有我深入到佐治亚海岸的圣凯瑟琳岛。圣凯瑟琳岛尚未开发,主要用于科学研究,是我们行程中到访的第5个岛。我的同事,地理学家迈克尔·佩奇(Michael Page)头一天才加入我们。2012年7月他和我一起在圣凯瑟琳岛找过短吻鳄的巢穴。我们记录了几十个靠近水边的洞穴,其中很多都寄居着短吻鳄。有些时候我们能够确认这些大型洞穴的寄居者,因为看见短吻鳄在附近游泳或者目睹它们冲进洞穴。还有一些洞穴,我们发现了短吻鳄的形迹以及它们交错进入洞穴时尾巴留下的拖痕,我们明白不要靠近那些洞穴。
然而,这次的巢穴口并没有出现清晰的警示痕迹。当吼叫加嘶嘶声从洞穴里面传出来,迈克尔正站在洞穴后面,而我几乎站在洞口前。那天早上我们看了大约10个鳄鱼洞,里面都是空的。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在靠近这个洞口的时候,确认上的偏差影响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对于这个洞穴的记忆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误判,2012年夏天迈克尔和我检查过它,当时根本没有鳄鱼的踪迹。那次我们拍照并测量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巢穴,同时用GPS设备记录具体的位置。我们记得这个特殊的巢穴,因为它的洞口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入口,超过1米宽,40厘米高。当时如果我犯傻的话,肯定就直接爬进去了。
除了大小,我们对这个洞穴印象更深刻的是它的位置,在树林的中央。大家可能都知道,短吻鳄一般居住在水里,但那个巢穴周围没有湖泊、池塘或小溪流,巢穴周围的林地上铺满了干松针。而且,这个巢穴和附近其他几个巢穴位于曾是人工挖掘的河道的岸边。于是,迈克尔和我就想当然地推测:过去什么时候,或许在几十年前,这个河道被淹,短吻鳄不得不转移到附近重新开建巢穴。后来,干旱和当地水文的其他变化一定改变了这个地区的供水,短吻鳄又游去了别的地方。
我只是刚刚开始向学生解释这是由前几代已经死去的短吻鳄建造而又被遗弃的另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它有着短吻鳄以前在水生环境下的生活痕迹,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陆地环境。这是个不错的假设,但却活生生地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被遗弃的家”里面住着两米长、全身盔甲、坏脾气的鳄鱼。
学生们开始踏上一条误解的路,认为这个大洞里没有鳄鱼。我一看到巢穴,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来不及和学生们介绍就兴奋地大步走向入口。有几个学生往后站,感叹着洞口的大小,盯着洞下的黑暗,似乎就是一个无底的神秘深渊。身后的变焦镜头和数码快门声告诉我,他们已经拍了很多照片。看到他们对洞穴感兴趣,我非常开心。
突然,一个学生说:“我看到里面有牙齿。”这个声音惊醒了我。
“牙齿?”我回问道。
“是的。”她回答,其他同学纷纷点头。
“什么样的牙齿?”我接着问。就像个典型的古生物学家,我当时想象着是一个空的头盖骨或下颌,而不是一个长着牙齿的活物。
“我不知道。会是蛇吗?”
“当然,有可能。”我以前在短吻鳄的巢穴里看到过蛇。而且,和一般书里写的考古学家不一样,我喜欢蛇,盼望着能在巢穴里找到一条。“不过如果是蛇,你看不到它的牙齿。”我回答着,脑子里还在琢磨这教学计划的变化。边想着,我又向洞口靠近了些,这个行为激发了巢穴中可怕的吼叫和嘶嘶声。
我抬头看着迈克尔。可能当时我一脸的不相信,但是我的脸色一定是在问他:“我们现在怎么办?”
迈克尔正一只手拿着GPS设备,他微笑着,抑制不住对我们窘境的幸灾乐祸,说:“估计我们得把这个洞标为‘已居’。”
巢穴:生存的多面屏障
这次短吻鳄事件改变了我的认识,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野外考察的狂欢,而是与潜在的危险对象的近距离接触。这个认识源于我们所了解的短吻鳄常识,它们是鳄目动物及两亿多年前同族的后代,当时恐龙还盛行,蹦跳、搏斗、觅食、求偶、排泄,在地球上留下它们的标记。而当6 600万年前,陨石落入地球,这一灾难和其他问题一起引发了各地生命的毁灭性危机,无论在海洋还是陆地。结果,所有的恐龙(并没有成为鸟类)死亡,只留下了它们的骨骸和行动的遗迹。
与此同时,短吻鳄和其他种类的鳄鱼继续发展,还包括乌龟、蜥蜴、蛇类、鱼类、昆虫、蚯蚓、哺乳动物以及其他我们目前认为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它们在基因或行为能力方面的独特性才足以帮助它们生存下来,而恐龙却没有。
我们先来说说鸟类。家里有5岁孩子的人都知道,并非所有的恐龙家族都灭绝了,有一些进化成了现代的鸟类。最早的鸟类祖先是大约1.6亿年前的兽脚亚目恐龙,大多数兽脚亚目恐龙是两条腿的食肉动物,如电影中的迅猛龙和暴龙。迄今为止,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大约40种带羽毛的兽脚亚目恐龙,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断言:从侏罗纪晚期到白垩纪时期(大约1.6亿到6 600万年前),大多数兽脚亚目恐龙是有羽毛的。6 600万年前,带羽毛、飞行的鸟类恐龙在物种灭绝中存活下来,而其他所有的恐龙则全部消亡。
有趣的是,就在圣凯瑟琳岛和佐治亚海滩的其他地方,我和学生们亲眼看见了鸟类和鳄鱼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白垩纪。有些岛屿内部有一些池塘,形成了更小的小岛,在那里体格高大的涉水鸟类,如鹳、苍鹭和白鹭,在树枝上筑巢,远远高出陆地和水面。它们的巢穴不仅受到母鸟的保护,还受到看似不可能的盟友短吻鳄的保护。由于短吻鳄在池塘里游泳并在附近的洞穴里休息,它们会对浣熊或其他哺乳动物产生相当的威慑,不让它们以为自己可以袭击鸟巢,享用煎蛋早餐。然而,这样的交易,根本就是浮士德式的交易。
作为一种类似黑手党的回报,如果一只孵化出来的鸟从巢里掉到岛上或池塘里,这倒霉的小鸟就成了一种简单的食物,因为任何鳄鱼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然而,对于鸟的父母来说,这种残酷的补偿比被残忍的浣熊吃掉整个鸟蛋蒲包要好得多。因此,这些鸟类和短吻鳄可能共同进化出它们各自的行为,而它们的祖先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做出了相互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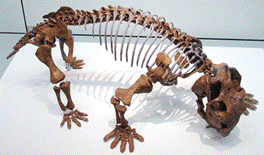
许多成功的动物谱系中包括穴居行为。一具水龙兽的化石骨架具有粗壮的前肢,像铲子一样的面部,以及其他用来挖掘的各种适应能力。这一物种属于合弓纲类爬行动物,几乎所有的此类爬行动物都在大约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灭绝。而幸存下来的物种中很多是穴居动物,洞穴有助于它们的存活,哺乳动物最终从这个谱系进化而来
那么现在我们来关注短吻鳄,特别是那些在圣凯瑟琳岛上的鳄鱼。2013年我和学生们一起造访的时候,那里的短吻鳄在过去几年一直遭受着干旱的煎熬,几十年中,岛上降水量减少,整体形势更加严峻。这意味着短吻鳄的正常栖息地――淡水池塘和其他湿地――已经萎缩,留给它们栖息的地方更少,只能通过捕杀鱼类和其他动物为生。有人可能会想象着这样的低水供应和可怕的条件会使鳄鱼的骨架散落在干燥的整片土地上。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非常活跃,在巢穴中度过了更多的时间。短吻鳄很可能在池塘边、水渠边以及其他湿地的边缘挖出这些巨大的巢穴。一旦湿地消失,被草原和森林所取代,这些巢穴却仍然存在。然而短吻鳄依旧可以回到这些巢穴中,一些它们仍然使用的巢穴与地表下的地下水位相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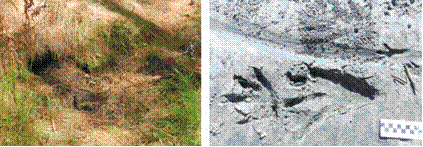
在短吻鳄巢穴外发现的鹿骨盆显示的证据表明,巢穴可以帮助短吻鳄捕猎(左)。在佐治亚州海岸的圣凯瑟琳岛上,一场风暴在盐沼附近形成的沙质区域显示了鳄鱼的足迹和尾巴的拖痕。这些痕迹指标可以用于测定动物的分布和栖息地的使用情况,并说明短吻鳄并不只停留在淡水地区,一个招潮蟹的巢穴旁也有尾巴的拖痕(右)
这些地下“湿地”可以使短吻鳄的皮肤保持湿润,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好处。例如,考虑到这些巢穴在一个淡水资源变得更加珍贵的岛上可以保持水源,它们也为其他动物,比如哺乳动物和鸟类,提供了诱人的水源。因为口渴,它们齐刷刷地把自己送到了鳄鱼们的嘴边。短吻鳄只要在洞口等待,觉得猎物够大就直接捕抓。我和学生们在同一次野外考察中发现了短吻鳄使用伏击捕猎策略的证据:两个洞穴的外面都有刚捕杀的猎物尸体。一个洞穴里有一只秃鹰的遗骸,它的骨头和羽毛都插在洞口;而距离另一个洞口大约1米远的地方则有一只浣熊的遗骸,离浣熊再有1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只死去的秃鹫,两具尸体血迹未干,说明它们接连被捕杀。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到,一旦浣熊被抓住,身体被捕食一部分后,其血腥气就会引起秃鹫的注意,于是一下就为短吻鳄提供了一顿两道菜的大餐。
同样地,岛上一些地方年代久远、被长期遗弃的巢穴前都有一堆堆的骨头,主要是鹿和浣熊的残骸。所有这些痕迹的证据告诉我们,如果有必要的话,短吻鳄可以从水生转为陆地捕食,好比鲨鱼决定要变成狮子一样。短吻鳄令人惊讶的行为转变和适应性通过它们的巢穴来实现,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巢穴变成了万能的狩猎小屋。
除了能让居住者皮肤保持湿润并使它们伏击猎物,巢穴还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功能:保护作用。例如,圣凯瑟琳岛的干旱条件加剧了闪电引发的森林和草原大火的可能性。果然,2012年夏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圣凯瑟琳岛的部分地区。这个地方有相当多的短吻鳄巢穴,岛上的管理者罗伊斯·海斯(Royce Hayes)给它起了个绰号叫“神经中枢”。他惊讶地发现,在一层野火灰上发现了新鲜的短吻鳄的足迹,这是那些在大火中安然生存于巢穴中的鳄鱼爬行留下的痕迹。
如果这种鳄鱼巢穴还不足以让你觉得它们能起到保护作用,那就想想鳄鱼宝宝吧。没错:可爱的小鳄鱼宝宝刚孵出来的时候,大小正好可以放在普通成年人的手掌上。等到后来,就像人类的孩子最终会变成青少年一样,它们长大成了“怪兽”。尽管如此可爱,一只鳄鱼宝宝还是被几乎所有比它大的东西当成开胃菜,包括其他鳄鱼。因此,这些小宝贝需要防御,这部分主要由它们的母亲提供保护,巢穴也可以。鳄鱼妈妈们在孵化后的两年里都要和它们的孩子待在一起;如果巢穴在附近,它们不仅在巢穴中获得大量淡水(短吻鳄宝宝的需要),巢穴也是它们保护幼崽免受伤害的庇护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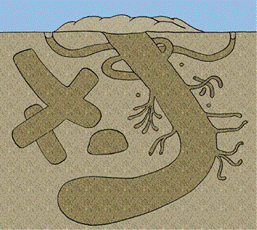
另一个狂热的挖掘者哥法地鼠龟的地下洞穴插图,显示了一个通向居室的大转弯。较小的洞穴被其他动物延展,比如老鼠和昆虫。图的左侧是部分坍塌的乌龟洞穴
我多次看到(或引发了)后者的行为。走在巢穴附近或小池塘边,短吻鳄宝宝会发出警报,由一系列高音调的咕噜声组成。这些声音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你可能会死,因为一只巨大的鳄鱼妈妈正在附近,而且知道她的孩子正处于危险之中。一旦小鳄鱼发出了警报,鳄鱼妈妈就会爬或游向巢穴,为她的宝贝带路。小鳄鱼还会发出咕噜声,它们排成一行,努力地一起向巢穴里游去,和妈妈在一起。到那时,她将会在一个非常靠近巢穴入口的空间里转过身来,准备保护她的孩子免受任何可能试图给它们带来伤害的人类或其他任何东西。在一些时候,我看到了鳄鱼妈妈的巨大头颅就在巢穴的入口后面,不惧你的靠近并等待你来测试她的进化后的能力。
巢穴保护着所有年龄段的短吻鳄,从寒冷的冬季到炎热的夏季。大多数人都知道,短吻鳄是冷血动物或者说变温动物。这意味着它们不能调节体温,必须依靠周围的环境将自己保持在一个生命允许的温度范围内。对于短吻鳄来说,理想的温度大约是27℃到32℃;超出或低于这个范围的温度对它们来说都会有问题。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与任何现代鳄鱼相比,短吻鳄可以生活在离赤道更远的地方。在北美,这些大型爬行动物可以生活在北卡罗来纳以北的地方,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就是靠巢穴。
这些洞穴通过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的平均气温来获得“金发姑娘效应”,以保持全年合适的温度。在佐治亚海岸,夏天的温度很容易超过32℃,水温接近热水浴缸,这时候短吻鳄就会躲到洞穴里避暑。相反,我也看到过体态巨大的短吻鳄在12月严寒冰冻的日子里晒太阳,说明附近有它的巢穴,可以让它保持足够的温暖,在户外享受阳光疗法。人类探察洞穴者也同样描述了地下效应的缓和作用;在夏天和冬天,他们分别享受着凉爽、温暖的洞穴内部的感觉,而这个洞穴的温度实际上全年保持一致。
所有这些把我们带到野外考察课堂上不期而遇的穴居者,同时巧妙地回答了一个完全合理的科学探究:一只体格巨大的成年短吻鳄在森林中到底做什么?
还记得我说过3月份要再去拜访吗?我们行程的时机说明,这个巨大的生物很有可能在冬天的什么时候爬进了巢穴,那时候温度已经降得相当低,它需要很长的时间维持温暖才足以存活。春天的时候我们在佐治亚海岸,当时室外温度接近于短吻鳄最合适的27℃~32℃,而不是严冬的冰冷。然而3月初的平均温度在10℃左右,想让短吻鳄从临时的庇护所里出来,温度还不够高。佐治亚这个地区全年的平均气温差不多是20℃,也就是说,如果你全年都住在地下,不需要设置恒温器,因为会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当外面的天气降到冰点以下时,这只大鳄鱼和它的许多同胞可能整个冬天都待在巢穴里。探察洞穴者和其他地下探险爱好者根据他们的经验得知,短吻鳄通过自然选择来解决问题。
考虑到洞穴的多方面用途,很容易就明白了如何简单地描述巢穴在短吻鳄进化史上起到的作用:没有巢穴,就没有短吻鳄。只要快速地浏览短吻鳄的近亲,例如中国短吻鳄(扬子鳄)在河岸上挖出一些通道来制造巢穴,以及其他在洞穴中生存的鳄鱼,那么这一大胆的说法就会得到支持。事实上,所有鳄鱼物种中有超过一半在环境压力下,比如干旱,会挖掘并生活在巢穴中。和短吻鳄的数量比一比,我们再看看多少蝾螈、青蛙、蟾蜍、乌龟、蜥蜴、蛇以及其他变温动物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几乎所有这些动物都通过在地下过冬或其他的保护来完成这一壮举。即使是自我升温的恒温动物,也就是鸟类和哺乳动物,它们在地表以下寻求庇护,也有可能在冰冷或炎热的天气状况下死亡。简而言之,除非它们移入地下,不然这些动物无法继续存活。
地下进化

当然,洞穴并不仅仅局限于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图中的小企鹅现身于塔斯马尼亚的布鲁尼岛上的一处洞穴,是很多其他穴居地下的动物之一
我们从研究短吻鳄的巢穴得到的这些见解表明,至少现代短吻鳄和鳄鱼的祖先,或许还有它们的鸟类同伴,很可能利用巢穴来应对过去的环境危害。举一个穴居鸟类的例子,想想那些迷人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不可阻挡的、吃着磷虾的前行者:企鹅。所有的企鹅物种都生活在南半球,所有的北极熊都生活在北半球,这意味着你唯一能看到北极熊吃企鹅的地方是在一个管理不善的动物园里。然而,尽管生活在南极洲的企鹅千篇一律,它们聚集在一起取暖,但大多数物种实际上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此外,超过一半的企鹅物种都生活在洞穴中,而且你能猜到,它们利用洞穴来抚养雏鸟、保护自己和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避免受到外部恶劣环境的影响。(顺便说一句,已知最古老的化石企鹅可以追溯到约6 200万年前,就在它们的非鸟类恐龙同族灭绝之后。)因此,短吻鳄的巢穴绝不是一种独特的洞穴,它的存在令巢穴的制造者存活足够长的时间,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同时也使基因传递者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对许多动物来说,洞穴拯救并延长生命,同时也成为动物家庭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记住“洞穴即生存”的主题,以防你仍然被“短吻鳄-鳄鱼-鸟”在非鸟类恐龙灭绝阶段成功演变的故事所吸引。许多哺乳动物都是非常优秀的穴居者,这种能力甚至比短吻鳄、鳄鱼和鸟类的地质年代出现得还要早。这些毛茸茸的脊椎动物的祖先被称为哺乳类形式,演化到大约2.2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那是在恐龙出现之后。哺乳类形式的祖先合弓纲爬行动物更是起源于远古时期,在距今3亿年前的石炭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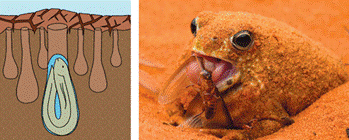
来自于泥盆纪时期(约4.2亿到3.6亿年前)的肺鱼洞穴化石显示,这些动物会在潮湿的泥土中蠕动,在冬天或干旱的时候,将自己包裹在黏液茧中冬眠(左)。现代两栖动物也同样利用它们的挖掘技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像这只沙漠里的蟾蜍一样,它从澳大利亚沙丘上的洞穴中跳出来,捕捉昆虫(右)
一旦合弓纲爬行动物进化,比如异齿龙,整个二叠纪时期(约3亿到2.5亿年以前)它们在适应并控制陆地环境方面非常成功。令人遗憾的是,二叠纪末期,几乎所有的物种都灭绝了,这又被称为“大灭绝”,因为全球变暖和其他因素导致95%的物种与它们干涸的基因库告别。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几乎”,言下之意还有少数没有灭绝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三叠纪。从这些幸存的合弓纲爬行动物开始,哺乳动物进化了,他们的后代在三叠纪末的另一次大灭绝中幸存,在非鸟类恐龙的全盛时期一直存在,但没有繁荣发展。接着,6 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恐龙在大灭绝中全军覆没,哺乳动物保留下来。这样的成功保全了我们的灵长类动物血统,其中的一些学会了如何控制火,追踪狩猎动物,识别有用的植物,了解天体,最终用表情符号传递情感。
洞穴不仅仅开始于合弓纲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而且作为生存工具也要追溯到更远的时间。例如,在泥盆纪和石炭纪时期(4.2亿到3亿年前),肺鱼和两栖动物挖掘并生活在洞穴中。这些动物的骨骼化石甚至在化石洞穴中被发现,将这种行为与现代的穴居肺鱼、蝾螈、青蛙、蟾蜍以及其他类似的两栖动物联系起来。穴居行为使这些依赖水的动物能够生活在沙漠中或者避免干旱带来的最坏影响。一些肺鱼、青蛙和蟾蜍自埋后,就会待在地下,数月或数年之后变得懒散,而一旦水源充足,它们又会重新跳出来。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洞穴里的肺鱼和两栖动物化石并没有存活下来。然而它们的亲属则生存下来,并将穴居能力传给了后代,这一切都是进化上的问题。此外,所有这些动物都是由水里的动物进化而来,它们拍翅、滑行、爬行或者在异域海岸登陆。这些水生动物是如何成功克服从水里出来后所面临的陆地环境的干燥化影响的呢?当然,洞穴帮了大忙。
这些穴居无脊椎动物的演变史完全改变了全球环境,甚至影响了气候。
后来,各种大小和不同形状的脊椎动物洞穴也为许多其他物种提供了微生物栖息地,今天最好的例子就是地鼠龟和它们的家。这些看起来不太给人印象深刻的乌龟,不比典型的餐盘大多少,它们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洞穴挖掘者,它们挖空的隧道长度可以超过10米,深度3米,以远离对它们造成的伤害。它们漫长的隧道里也可以同时容纳近400个物种群居,从昆虫到蛇,经过无数代洞穴的发展之后,至少有几个物种已经进化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地鼠龟洞穴中生物多样性的地下“热带雨林”,暗示了脊椎动物洞穴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在当今许多生态系统中维持生命的平衡。
但关于脊椎动物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地球上真正的霸主是什么,比如蠕虫和昆虫?其他几乎适应了所有陆地和海洋环境的无脊椎动物怎么样?现代无脊椎动物还生活在洞穴中吗?它们的祖先也生活在洞穴里吗?当然,过去和现在它们都是生活在洞穴里,就像任何拥有院子的人,在公园里散步,沿着海岸散步或者坐在蚂蚁窝上。这些洞穴留下的自5.5亿多年前的动物的进化历史记载,随着他们从地表生活过渡到深穴聚居,它们从深海环境转移到浅海洋底部,大海到淡水池塘和小溪,从水体到陆地。这些每天观察到的地面上无数洞穴背后,更大的图景是这些穴居无脊椎动物的悠久历史完全改变了全球环境,从最深的海洋到最高的山脉,甚至影响到大气和气候。简而言之,我们这个星球的整个表面都是建立在一个复杂而不断进化的洞穴系统之上,它控制着我们生存的本质。
资料来源 Amercian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彦 隐
――――――――
本文作者安东尼·马丁(Anthony J. Martin)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足迹化石学家,也是2017年出版的《地下进化》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