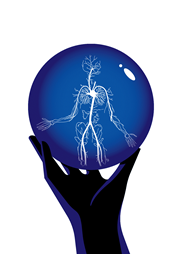我们比以前更早发现肿瘤,但是我们能预测它们是否会变得很危险吗?我们对癌症这种疾病一直予以极大关注,但是它的宿主,即癌症产生的“土壤”而不是“种子”,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它是否会在未来给我们带来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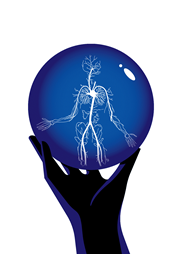
2011年夏天,密歇根湖的湖水变得清澈透明,一道道倾斜的光柱,就像来自UFO的探照灯一样,照亮了整个湖底,从上方看去,湖底一艘古代沉船赫然入目。但是,人群中的惊喜很快被恐慌代替,湖泊不应该看起来像游泳池一样清澈。生物学家研究考察后发现,通常生长在湖中、搅动湖水让湖水变得混浊的无数浮游生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猜测,湖中存在某种贪婪的生物,导致这些浮游生物渐渐消失。可能的罪魁祸首是软体动物:入侵生物斑马贻贝与其表亲斑驴贻贝。
有机体的“入侵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进入美洲水域的亚洲鲤鱼是一种凶猛的入侵物种,但生活在亚洲一些水域中的这种鲤鱼却并没有特别的入侵性。如今入侵英国一些珍贵园林中的日本虎杖,也叫日本紫菀,是一种生活在日本的蓼科杂草,在日本却并不被认作杂草。某种入侵物种在某种环境中会是很平静的“居住者”,但它们的温顺只是基于某种环境条件下的温顺,当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会突然变得极具攻击性。
2017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走在芝加哥密歇根湖岸边,想到了贻贝、虎杖,还有癌症。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座城市参加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年度会议――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癌症会议(ASCO)。我知道,会议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于讨论癌细胞的内在特性以及针对癌细胞的方法上。然而,对于癌症来说,这些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像我们知道我们要应对的是某种软体动物,但我们还需要了解它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湖泊环境中。
癌转移的“种子与土壤”理论
一个由来已久的观点认为,癌症的转移依赖于局部生态位。1889年,一位名叫斯蒂芬·佩吉特(Stephen Paget)的英国医生开始研究了解癌症“初级生长及其衍生次生生长的情况”,斯蒂芬的父亲詹姆斯·佩吉特(James Paget)是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叔叔是剑桥大学的医学教授,年轻的佩吉特继承了父辈的智慧。在老佩吉特的时代,癌被认为是一种像墨水斑迹一样从原发病灶向外扩散的恶性疾病。外科医生笃信这种中心扩散理论,即癌症像污迹一样从中心肿瘤块向外传播,他们建议对癌症患者进行彻底的肿瘤切除手术,该理论构成了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提出的“激进”的乳房切除术的知识基础。但当佩吉特收集了735名死于乳腺癌妇女的病例档案后,他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转移模式,癌症转移似乎并非是从中心向外蔓延的,而是离散型的,它们会转移至解剖学上的远端。而且这种扩散模式远非是随机发生的,癌症对某些器官有一种奇怪而强烈的偏好,佩吉特发现,在300例奇怪的癌症转移病例中,转移到肝脏的有241例,转移到脾脏的有17例,转移到肺部的有70例,癌细胞跨越了解剖学上的大片区域转移到了它们特别偏好的器官。
为什么肝脏是癌细胞转移的一个适合生存之地,而在血液供应、大小和接近度方面都极为相似的脾脏,却似乎对癌细胞入侵有相对较强的抵抗力呢?佩吉特经深入研究后还发现,癌细胞的生长甚至偏爱于器官系统中的某些特定部位,例如,骨骼也是乳腺癌转移的常见部位,但并非每一块骨头都具有同样的易感性。“有谁见过手骨或脚骨被继发癌症侵袭的?”他问道。
佩吉特以“种子和土壤”来形容这种现象。种子是癌细胞,土壤是癌细胞或在那里兴旺繁殖起来或入侵失败的局部生态系统。佩吉特的研究集中于人体内的转移模式,某些器官由于受到癌细胞的青睐更易感,而某些器官则由于其特性或在体内的位置而逃过劫难,简言之,取决于局部的生态环境。然而,“种子与土壤”模型的逻辑最终引发了一个关于人体整体生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的身体会成为癌细胞的易感生态位,而有的人则不会呢?
佩吉特将肿瘤转移的问题定义为癌症细胞与其环境之间的病理关系,但他的研究成果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但也有例外,癌症转移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艾塞亚·菲德勒(Isaiah J.Fidler)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开始研究“机体组织和肿瘤之间的关系”,菲德勒的研究表明,肿瘤是由数以百万计细胞组成的非匀质混合物,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能力离开原发肿瘤,与另一个器官的“土壤”形成一种开发新“殖民地”的联盟,从而启动了癌症转移过程。同一时期,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之后进入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米娜·比塞尔(Mina Bissell)也开始对癌细胞在它们能够生存或不能生存的多种器官中的微环境进行研究调查,以寻找确定有利于或不利于癌症生长的环境因素。她发现这种环境因素对于癌症产生至关重要。
然而,肿瘤学作为一个整体仍然被一种更简单的模型支配着。当我还是波士顿的医学专科学生时,一个寒冷的冬天,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对一系列的骨转移癌(乳腺癌、肺癌、甲状腺、肾癌、前列腺癌)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癌转移如何产生的心理意象。癌细胞通过血管向外散布开来,“攻击”器官,开始萌芽并活跃生长起来。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我巡查癌症病房时,医生们的话强化了我的这个想法。“这个肿瘤正在侵袭大脑。”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室里对另一名外科医生低声说道。在他的这句话中,癌症是主语,是自主行动者、侵略者、驱动者,病人和他们的器官是宾语,是受众,受害者、是被动的旁观者。
在研究的思考模式发生变化时,人们仍然坚持这种说法。“癌症究其核心是一种遗传病。”麻省理工学院的癌症生物学家罗伯特·温伯格(Robert Weinberg)说道。于是,几十年来,生物学家一直在寻找导致癌细胞异常生长、新陈代谢、再生或行为的某些基因突变:met基因(癌转移基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癌症生物学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温伯格,都纷纷投身于寻找导致癌症转移的基因,比如说,乳腺癌细胞,是否因某种基因变异而导致它从乳腺部位逃逸至大脑中安家落户呢?
癌细胞入侵“择人而噬”
2001年,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癌症生物学家约恩·玛萨古(Joan Massagu)偶尔看到的一篇科学论文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癌症转移的看法,来自巴塞罗那的玛萨古头发已经花白,他花了多年的时间研究细胞生物学,阐明乳腺细胞向骨骼转移而不是向大脑转移的基因调控机制。随后他发现了30年前发表在杂志上一篇文章中一直未被注意到的一份重要证据,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雌性老鼠的卵巢蒂上移植了一个乳腺癌细胞囊,细胞生长形成了豆粒大小的肿瘤,然后研究人员用插管插入大静脉引流肿瘤,并每隔几小时从静脉抽一次血,对肿瘤上脱落的癌细胞进行计数。
结果令调查人员困惑不解,他们发现,平均而言,肿瘤脱落进入血液中的癌细胞每1毫升血液中达2万个,相当于每24小时每克肿瘤脱落近300万个细胞。在一天时间中,肿瘤减少了将近1/10的重量。后来用更复杂的方法对动物肿瘤进行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是极为自然发生的,证实了肿瘤细胞不断脱落并进入血液循环。人体的局部肿瘤脱落率较难研究,但现有的动物研究成果倾向于证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将癌症转移想象为一个行进中的问题,”玛萨古告诉我说,“癌细胞行向骨骼,癌细胞行向大脑。”他的重音放在每一个动词上,脸上充满了兴奋的表情。“是的,行进这个词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找到让细胞从肿瘤中分离出来进入血液和淋巴结的究竟是什么。但如果人类原发肿瘤细胞不断脱落,如果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形成明显的转移,那么每一个病人的全身都存在无数明显可见的转移癌细胞。”真正的难题不是为什么有些癌症转移会发生在某些癌症患者身上,而是为什么癌症转移不会发生在所有患者的身上。
“唯一能解释癌症转移只发生在部分患者身上的原因,”玛萨古说道,“是设想细胞死亡或细胞休眠的数量极为庞大,这一因素对癌细胞转移起到了限制作用,肿瘤脱落下来的细胞有的死亡,有的停止分裂,处于休眠状态,当肿瘤细胞进入血液循环时,它们几乎都已经大量死亡,只有少数能到达它们的目的器官,如大脑或骨头。”
但即使是那些抵达目的地的癌细胞,也将面临生存在一个陌生的,甚至是一个可能不适宜生存的环境中。玛萨古推断,那些幸存下来的细胞很可能都处于休眠状态。“临床上可见的癌细胞转移,那种我们可以用CAT扫描或MRI检测到的,只能是那些从休眠中被激活并开始分裂的细胞。”他说。恶性肿瘤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癌细胞扩散的问题,还是癌细胞是否能在新环境中扎根并繁荣起来的问题――如果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2012年春,当玛萨古和其他人还在寻找潜伏癌细胞的时候,达特茅斯流行病学家吉尔伯特·韦尔奇(Gilbert Welch)正全神贯注于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早期筛查并不理想的预期效果。韦尔奇告诉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极端例子,一个似流行病又不是流行病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5年前的韩国,当时医生们开始积极进行甲状腺癌的筛查工作,首尔的基层医疗机构都配备了小型超声设备,并开始对医生进行如何发现疾病的早期症状的重新培训。当发现一个可疑的小瘤时即进行活检,如果病理报告呈阳性,病人的甲状腺将被切除。
甲状腺癌的官方发病率,特别是一种被称为乳头状癌甲状腺癌的亚型开始在这个国家大范围迅速蔓延开来。到了2014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是1993年的15倍,成为这个国家被诊断出的最普遍的癌症。用一位研究人员的话来说,似乎“甲状腺癌之海啸”突然袭来。数十亿韩元投入甲状腺癌大流行的治疗,成千上万手术切除的甲状腺被扔进了手术垃圾桶里。然而,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并没有因此降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医学上的错误:在显微镜下观察,可疑的小瘤结节完全符合甲状腺癌的标准。但病理学家发现,这些小瘤结节几乎没有致癌倾向,患者并没有被误诊,但却是过度诊断,这指的是肿瘤确实被发现,但不会产生临床症状。
对韦尔奇来说,如果对死亡率未能产生相应的影响,甲状腺癌或前列腺癌诊断率的飙升是一种警告: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癌症筛查运动扩大了疾病的发病率,却没能告诉我们,针对任何特定的病例,是否需要治疗,早期检测告诉我们何时发现有何种癌症产生的可能性,但同样不能告诉我们是否需要治疗。为什么有些癌症会扩散并导致死亡,而许多肿瘤比较“温顺”,不会扩散呢?这些至今都还是未解之谜。
2012年3月的一天,韦尔奇飞往华盛顿参加一个癌症转移会议。这是一个阴沉刮风的上午,韦尔奇坐在一个会议室里,癌症生物学家会聚一堂,但韦尔奇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外来物种。他告诉我说,“我研究的是人口中癌症发生的模式和趋势,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都是在显微镜下观察癌细胞转移的生物学家,我不知道这与人类癌症的人口趋势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为什么我会来参加这次会议。”
然后,他手中的咖啡微微晃动,屏幕上放映的幻灯片让他赫然动容,幻灯片上讲述的是密歇根湖外来生物斑马贻贝和斑驴贻贝的侵袭事件。幻灯片的解说者是密歇根大学的肿瘤学家肯尼思·皮恩塔(Kenneth Pienta),斑驴贻贝危机事件与癌症袭击似乎是极为相类似的一种行为。研究人员需要将这种侵袭性视为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病理关系,而不是将这种侵袭性视为癌症固有的特性。“癌细胞与宿主细胞一起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皮恩塔提醒道,“最初,癌细胞是一种侵入新的生态位或新环境中的入侵物种,但最终,在癌细胞与宿主细胞的相互作用下创建了一个新的环境。”因此,不要问癌症对你做了什么,而是要问你对癌症做了什么?皮恩塔说道。
关注“土壤”问题
谈到癌症生态学,皮恩塔提出要更多关注“土壤”的问题。患有原发性乳腺肿瘤的女性可以假设是被困在了一场无声而激烈的战斗中,肿瘤学家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研究探讨这场战斗的可能结果:如果这位妇女败了,她将死于癌症转移,但如果癌症败了呢?也许癌细胞会转移并试图侵入新的生境,由于免疫系统的抵抗,以及其他生理学上的挑战,大多数癌细胞会死于转移途中,但大浪淘沙下幸存下来的少数癌细胞,单个的或成簇的,在这场远征中幸存了下来,仍然要经受新的陌生环境的考验,就像落在盐滩上的种子一样顽强地生根并成长起来。
1992,一位50多岁的澳大利亚高中教师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瘤。恶性肿瘤从一开始的一道黑色条纹从他的左腋下一直延伸到整个躯干。在确诊后的几周时间内,肿瘤的边界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个边缘变灰,另一个边缘萎缩。“他这种情况是一种典型的自然消退,通常是癌变受到免疫系统控制的信号。”这位患者的儿子大卫·亚当斯(David Adams)告诉我说。原发性黑色素瘤被手术切除,未见转移,而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也在他50多岁发现原发性黑色素瘤时,他的大脑里已有了明显可见的转移癌。
大卫·亚当斯在加入英国剑桥的桑格研究所之前,是悉尼的一名遗传学家和生理学家。父亲的黑色素瘤驱使他选择走上了科研道路。那么是什么令黑色素瘤在某个宿主体内退缩消失,而在另一个宿主体内却变得极具攻击性呢?亚当斯在医学文献中偶尔会看到一些关于黑色素瘤病例与捐赠肾脏有关的报道,例如,某位病人,我们且称他为D.G,他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瘤,通过手术切除治疗成功,几年后被认为非常健康的D.G.捐肾给一位朋友,医生用了常规的免疫抑制剂防止肾脏出现排斥反应。然而,几周后,这位朋友的肾上开始出现了许多星星点点的黑色素瘤,黑色素瘤正是来自D.G.的细胞,于是捐献的肾脏不得不切除。而同时,奇怪而又令人惊异的是,供体捐赠者仍然健康,他的体内没有任何黑色素瘤的迹象。
从这一例子中,亚当斯意识到,原宿主环境在限制转移生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捐赠者的黑色素瘤细胞在捐赠的肾脏中本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类似于小鼠实验中发现的癌细胞休眠现象,而当“土壤”环境发生变化时,休眠细胞进入了某个免疫抑制受体的体内时,癌细胞开始生长。“想必是捐赠者的免疫反应限制了转移癌的生长。”亚当斯告诉我说。
2013年,亚当斯开始构思一个雄心勃勃的实验:确定抑制癌症的宿主因子。“在离我的办公室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是一个有许多转基因小鼠品系的‘动物园’,”他说,“研究人员利用这些小鼠品系研究基因变异对心脏或神经系统的影响。但我想我会问一个有点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同样的癌症植入这些小鼠品系,哪些小鼠体内转移癌会生长,哪些小鼠体内会抑制转移癌生长呢?”
这是传统实验方法的巧妙转换。几十年来,生物学家一直在进行改变癌细胞基因的实验,并将癌细胞注射到几种标准品系的小鼠体内。癌症生物学家通过让“不同癌症进入同一品系”的实验观察癌症基因的改变会如何影响癌细胞的生长、新陈代谢和转移。宿主基因组的不同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亚当斯的“同一癌症进入不同品系”的实验将注意力从“种子”转移到“土壤”中。
亚当斯特别感兴趣的是宿主基因,而不是有可能对癌细胞转移产生影响的免疫细胞类型。2013年初,也在他的实验室里工作的博士后、亚当斯的妻子路易丝·凡德维登(Louise van der Weyden)将小鼠的黑素瘤细胞注射到几十个小鼠品系的体内,几周后,她计算了每种品系小鼠肺部可见转移癌细胞的数量,并迅速将数据送往亚当斯的办公室。
亚当斯回忆说,即使是在这一小群小鼠中,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老鼠体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转移癌细胞,密密麻麻如针孔般的小黑点,有的小鼠肺叶上由于转移癌细胞数量太多,已经明显变黑。然而,还有一些小鼠体内转移癌细胞很少,寥寥无几。亚当斯的书桌上方陈列着这些小鼠肺部的X光片子。他说,“同样的癌症在不同的宿主环境中会施加不同的作用。”
两年后,凡德维登给810个品系的小鼠注射了黑色素瘤细胞,然后观察每一个品系小鼠癌转移的生理机能。其中15个品系的小鼠产生了中度或极度抗性,这15个品系中有12个品系的小鼠有影响免疫调节的基因变异,这再次表明了免疫系统在癌症扩散和侵袭中的强大作用。在对转移癌有抵抗能力的群组中,有一个品系的小鼠表现出极为突出的抵抗力。暴露于研究用癌细胞剂量下,正常小鼠产生约250个转移癌细胞,而对癌细胞侵袭有抵抗力的小鼠品系平均只产生15到20个转移癌细胞,其中一些小鼠甚至几乎未产生任何转移癌细胞,在给它们注入癌细胞的两个月之后,这部分小鼠的肺部看上去还和原来一样健康,没有出现任何入侵转移癌细胞的迹象。
这是一种只针对黑色素瘤的抗肿瘤能力吗?还是一种众所周知会引发免疫反应的癌症?亚当斯和凡德维登对其他3种类型的癌症进行了实验测试:肺癌、乳腺癌和结肠癌。结果发现,这些小鼠品系对所有这几种类型癌症的转移癌都有抵抗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品系的小鼠带有一种被称为spns2的基因变异,这种变异基因通过一连串活动增加免疫细胞的数量,尤其是肺部的NK细胞,也正是玛萨古的实验室已确定为转移癌细胞的强大控制器的免疫细胞。
土壤与种子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最近最为成功癌症治疗创新之一是免疫疗法,激活病人的自身免疫系统并以癌细胞为靶子。几年前,具有开拓精神的免疫学家吉姆·埃里森(Jim Allison)和他的同事发现,癌细胞用特殊的蛋白质引发宿主免疫细胞的刹车机制,导致癌细胞不受抑制地迅速增长,用更适当的进化语言来说就是:阻断宿主免疫系统攻击的癌细胞的繁殖是一种自然选择和成长。埃里森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当用一些药物阻止某些癌症开发利用其制动蛋白时,免疫细胞就开始攻击它们。
这种治疗方法是最好的土壤疗法:不是直接杀死肿瘤细胞或以肿瘤细胞内的突变基因为靶点,而是通过警惕巡视机体组织环境的免疫细胞大军,改变宿主的生态学以达到抑制癌细胞的目的。但土壤疗法要考虑的并不只是免疫系统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多种多样的环境特征,如癌细胞相互作用的细胞外基质、肿瘤成功诱使为其提供养分的血管、宿主结缔组织细胞的性质,这些都会影响宿主机体组织的生态,从而对癌症的生长产生影响。
癌症,就像侵入五大湖的贻贝一样,在适宜的栖息地就会迅速增殖,同样也像贻贝一样,它们还可以创建一个帮助它们抵御敌人的微环境。种子疗法可杀死细胞,就像用可杀死贻贝的消毒剂喷洒湖水一样,而土壤疗法则可改变生境。当我问及亚当斯让他激动兴奋的那些有治疗潜力的临床试验时,他提起了一个不寻常的研究案例,研究人员可根据被诊断患有他父亲那样的原发性黑色素瘤的病人的血液,确定其遗传标记和免疫细胞组成,但通过它们之后发展趋势的研究,我们就可能知道哪些病人对某些癌症特别易感,更清楚哪些病人需要积极的治疗,我们可能会学到一些治疗方法,例如,如何改变易感患者的免疫学和组织学特征,使之类似于对癌症有抵抗力的免疫系统。
“癌症是细胞的一种疾病,就像交通拥堵是汽车的一种弊病一样,”英国医生、癌症研究员斯密瑟斯(D.W.Smithers)1962年在《柳叶刀》杂志上写道,“交通堵塞是因汽车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打破而造成的,而不在于它们自己正常运行与否。”史密瑟斯认为,细胞的关系决定了肿瘤的行为,他认为肿瘤学家必须考虑这个导致癌细胞激增的因素。“否认细胞在肿瘤生长环境中的重要性,就好比否定人们在社会群体生态学中某些问题的重要性一样。”他说。癌细胞是疾病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他的真正目标是超越肿瘤学对导致癌症的“内燃机”――细胞自动机及其基因――研究的执着,但一直到他去世后,他的观点才引起了肿瘤学领域的关注。
人体与疾病的整体生态
一旦我们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考虑疾病,我们就不得不问为什么有的人不生病。如果你是个医生,癌症遗传学的魅力在于它一下子就解释了癌症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对于生态学家来说,一切都是许多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组合。
我和麦克吉尔大学的入侵生态学教授安东尼·里奇阿迪(Anthony Ricciardi)谈起了这个问题,作为生物学家的里奇阿迪是在圣路易斯湖畔长大的,从圣劳伦斯河延伸出来的圣路易斯湖是斑马贻贝和斑驴贻贝转移到五大湖的入侵通道。“我对这个湖里的生命非常熟悉,小时候经常在湖里玩耍,后来求学期间也在那里做过研究。”他告诉我说,“以前我从来没有在湖里见过斑马贻贝,然后,在1991年6月的一天,在做一个研究项目的时候,我将一块石头翻转过来,发现了一只附在上面的斑马贻贝,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我才认出它是什么,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些。就在那个时候,我就预感到外来物种大举入侵就要到来。”
在我问起那些淡水贻贝大举入侵的行为时,他说道,“你必须对入侵生态学有所了解,这是如投骰子般的一系列赌博,大多数进入新环境的生物体都会失败,这通常是因为它们在错误的时间抵达了错误的地点,庞大数量的个体都将死亡。多年来有许多食人鱼被倾倒投入了湖中,但它们却无法在这里生存下来,因为这里的温度不适合它们。人们也曾将比目鱼这样的海洋物种投入湖中,但湖水的盐度不适合它们。”他的话,甚至他的语气,不由让我联想起玛萨古说过的一番话,他曾描述过癌细胞在转移过程中一波波大批死亡的情景。“不是某一个因素,而是一系列因素决定了贻贝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这里立足的。”他继续说道。
“但是,总的来说,你认为水温是关键吗?”我问。
“水温是一个因素,水化学也有关系。”
“那么说,是温度和盐度因素的结合?”
“还有含钙量,这也绝对重要。”
我记了下来,“温度、盐度、钙。”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一个适应性强的食肉物种。这些湖泊里的本地鱼几乎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蚌类,大多数鸭子以前也没有见过它们。”
“鸭子?”我疑惑道。
他叹了口气,仿佛要向孩子解释一个非常复杂的定理。“有许多促成因素,虽然其中一些因素显然比其他因素更重要,另外还有概率,都与具体的环境有关。”
原来如此。对于像我这样的癌症遗传学家来说,这是在挫败中学习的一种练习,每一次我试图锁定斑马贻贝入侵最主要的原因,却发现还有另一个竞争者。沮丧之下,我只得放弃。
也许我们都放弃了。考虑到我们的知识、方法和资源的局限,我们也许别无选择,可能不得不屈服于“奥卡姆剃刀”割裂的伤痛之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许多癌症生物学家在面对整个机体的复杂性时,很自然会专注于“病原体”:癌细胞。对转移癌症的研究似乎比对非转移癌症的研究更直截了当,从临床上说,研究那些没有生病的人是很困难的。我们的医生已经被疾病和健康的拨动开关模型所吸引:活检为阳性,验血为阴性,扫描未发现疾病证据,好细菌与坏细菌,等等。与此同时,生态学家谈论着营养、捕食、气候、地形组成的关系网络,所有这些都受制于复杂的反馈回路,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具体情境。对他们来说,入侵是一种反应式,甚至是一组复杂的反应式。
2017年6月于密歇根湖岸边召开的ASCO会议上,一个事实让我动容,只着眼于种子的研究正在为越来越多结合土壤筛选的研究腾出空间,甚至超过了围绕免疫疗法的热情。接受这种生态模式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获得对癌症的真正理解。
在肿瘤学领域,“整体论”已经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未经检验的偏方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如雄心勃勃的癌症研究者研究土壤和种子一样,我们看到了一种新途径的开端。它将我们带向“整体”的真正含义:将身体,生物体,其解剖学构造、生理等这一复杂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令人烦恼的多样性现象,促使医生不单要了解你的疾病,而且还要了解你与疾病关系的整体生态。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er
责任编辑 彦隐
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已出版了3部书,其中《万病之王:癌症的传记》(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曾获普利策奖。